达赖喇嘛:要脱离苦难深渊,必须先这幺做
地点是加州的新港滩(Newport Beach),时间则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。 达赖喇嘛在照相机快门声的和奏,和闪光灯断奏曲当中,走进为他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开的记者会现场。
达赖喇嘛在几小时前才刚听说自己获奖的事,仍处在要摸清头绪的阶段。一位记者问他,他打算如何安排当时总计有二十五万美元的奖金。他对这个奖项有这样一笔奖金,先是感到惊讶,接着便说:「太好了!我一直想捐一些钱给印度的一个痲疯病患村。」第二天他告诉我,他立即想到的是,如何把这些钱送出去。或许还可以送给饥民。
如同他常提醒别人的话,他不将自己视为一个受人崇敬的「达赖喇嘛」,而是一个普通的和尚。如此一来,他对这种来自诺贝尔奖项的钱,便不会有个人需求。
每当他收到一笔捐款,就立即转送出去。比方,我记得有次达赖喇嘛在旧金山参加一场有社运人士参与的会议。会议进行到尾声时,即公布该场会议的收支状况(非此种场合的一般正常程序)。门票收入在扣除支出费用后,还剩余一万五千美元。他当下就宣布,要将这笔钱捐给一个与会团体,用在奥克兰的弱势年轻人身上。大家听了后,无不大为惊喜。这个团体先前也受过鼓励,自行办过类似的会议。这件事是发生在几年前,之后也仍看到他持续这种即刻慷慨捐助的行动。
达赖喇嘛的想法则是这个时代的异数。他的存在似乎在对我们说: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,放鬆紧绷的神经,放下我执,抛弃以我为尊的心态,如此才能想到别人。
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前一晚,挪威来电说,他们的大使要亲自颁奖,已在前往颁奖的路上。但那通电话拨通时,已是晚上十点钟,早超过达赖喇嘛七点钟的就寝时间。
第二天早上,达赖喇嘛从清晨三点到约七点钟进行晨祷仪式(中间有早餐和收听BBC的休息时间),没人敢在这时间内打扰他,告诉他诺贝尔颁奖的消息。所以在他知道之前,新闻已先公布了。
同时间,他的私人秘书也忙着推辞,世界各地顶尖媒体蜂拥而入的採访邀约。这和几年前,记者对报导达赖喇嘛,常表现出意兴阑珊的态度,完全是南辕北辙。突然间,全球媒体的焦点都放在他的身上。世界性的主要电视网和报社,似乎都想沾上边来採访他。
虽然电话铃声不断地响,达赖喇嘛在那个早晨的作息仍然平静地进行,并指示秘书不要更动已安排好的行程,以及和神经科学家的会议时间。由于他不愿取消这个会议,其他行程的邀约因此被回拒,或是延后。他只接受让一个记者会,排进傍晚的行程中。
记者会开始前,将近一百位的记者和摄影师都已经到达当地饭店宴会厅,等待这个临时的记者会开始。他们聚集在会议厅里,摄影师拿出橄榄球球员争球的架势,无一不想占到一个靠近前方的最佳位置,抓住最好的摄影角度。
许多记者是从好莱坞就近派来。他们专门报导影视新闻,早已习惯接触影视界名人。而现在,他们所要面对的,却是一位淡泊名利,无意在新闻媒体镜头前过度曝光的另类人物。
在这个被自拍淹没的时代,许多人都觉得不打卡不行,每个所到之处,每餐所吃的食物,都要上传到网路。达赖喇嘛的想法则是这个时代的异数。他的存在似乎在对我们说: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,放鬆紧绷的神经,放下我执,抛弃以我为尊的心态,如此才能想到别人。
试想他对得到诺贝尔奖殊荣的反应。我刚好也出席他那一场记者会,因为我刚结束为达赖喇嘛和一群心理治疗师,还有社运人士主持的一场为期三天的对谈。那一场对谈的主题是关于:对人道关怀採取的行动。
在他知道得奖的那天,我为《纽约时报》访问他之后,我再次问他得奖感觉。他用他所谓的「破」英语告诉我说:「没什幺感觉。」让他感到开心的,反而是因为看到其他相关的参与者,表现出的开心感觉。他所呈现出来的反应,正是他的传统文化所称的「随喜」(Mudita)——因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。
想想他这种很有意思的性格。他的好友大主教戴斯蒙.屠图(Desmond Tutu),似乎特别能引发出他那张充满欢乐、淘气的脸庞。当两人聚在一起时,总如小男孩似地,互相揶揄。
不论聚会的性质为何,达赖喇似乎随时準备好逗人开心。
我记得在一场和一群科学家的会议中,他讲了一个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笑话(这种情形常发生)。他在过去已多次参与科学家的聚会。他告诉我说,这总让他想起一个有关喜马拉雅雪怪捉到土拨鼠的古老西藏故事。
雪怪站在土拨鼠洞穴的出入口,想等土拨鼠跳出来时,就可以立刻向前突击,将土拨鼠压着,好像坐在土拨鼠身上一样。但是当另一只跳出来时,雪怪又得站起来去捉另一只。而这时原来的那一只就逃走了。
达赖喇嘛笑着说,这个场景就像他在上完所有科学课程后的记忆一样!
还有一次,他在一所大学侧厅,等候和科学家的研讨会开始。会议前有一段由高中学生表演的无伴奏合唱做为余兴节目。当合唱开始时,达赖喇嘛悄悄地走上那个没有布置的舞台,在唱歌的学生们旁边张手飞翔,模样快乐得不得了。
这一段演出并不在安排的脚本中。那些準备好,要正式接待达赖喇嘛的研讨会成员和学校工作人员,站在后台不知所措。沉浸在自娱中的达赖喇嘛,向演唱的学生投以微笑,完全忘却那一群也对他微笑的台下观众。
在一个仅有受邀者可参加的会议中,二十四位执行长围着一张长桌坐,达赖喇嘛则坐在桌子的正前方。当他们在谈话时,一名受雇全程拍摄会议的摄影师,坐在达赖喇嘛椅子旁边的地上。他的长镜头不断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。
达赖喇嘛暂停讲到一半的话,神情饶富趣味地往下看着那名摄影师,然后要摄影师不如躺在地上睡一觉。会议结束后,摄影师拍了一张达赖喇嘛和那些企业领导人的正式团体照。
就在团体照完成,众人解散时,达赖喇嘛示意摄影师过去,接着就拥着他,和他拍了一张双人合照。
此类片段小插曲单独发生时,似乎很平凡。但当次数变成点点繁星般多时,就可以说明,达赖喇嘛独特的情绪反应以及社交方式。他对周遭的人富有同理心,充满幽默感,态度自然不做作,拥有将全人类当成都是一家人的一体感,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胸襟。他人生态度的特点不胜枚举。
他拒绝当一个假神圣伪善者的态度,还有性格上爱逗笑的小弱点,是我对他最啧啧称好的地方。他表达慈悲心时,总带着愉悦的心情,而不是冷峻的态度和空洞的陈腔滥调。
毫无疑问地,他的这些特质是透过从年轻时就开始用功研习,和潜心修行荟萃而来。他现在每天仍然保持研习和修行五小时的习惯(早上四小时和晚上一小时)。这些每日的研修,形塑出他的道德感,和他对外流露出的性格。
这种自律精神,也是他独特价值观的稳固基础。而这种价值观又让他酝酿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观。最后,他的真知灼见即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发光发热。
「若要脱离过去苦难的深渊,就要先扭转内心——弱化毁灭性的情绪,强化美好的人性,」达赖喇嘛说。
达赖喇嘛已经环游世界几十年,见过的人包括各种背景、各种阶层、各种长相——种种经历也因此造就他如此的眼界。他日常接触的人,从原籍来自巴西圣保罗,或南非索威托(Soweto),住在贫民窟里的归化公民,到州长或是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有。他的慈悲心,是他在接近这些广大群众时,始终不减退的动力。
他眼里所见的是人类全体——全都是「我们」,没有迷失在「我们」和「他们」之间的不同。在他提到「我们人类这个家庭」时,这个家庭所面临的问题,如富人与穷人间逐渐加深的鸿沟,或在支持人类生命的太阳底下,从事各项人类活动时,无法避免的崩坏衰退,对他来说,都是属于全球性的问题,凌驾国与国之间的界线。
达赖喇嘛从这些丰富的多元经验,打造出一个要将希望、动力,和凝聚力带给人类群体的计划。那是一张心灵地图,让我们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,了解这个世界,评估该做的事,以及如何打造共同的未来。
他对人性的观点,如同他对待自己的方式一样,是透过自身实践和自我察觉来体现。此种做法推翻了今天许多发展过度自由的价值。他洞见到一个更能付出关怀,更有慈悲心的世界:一个在面对集体挑战时,能以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的世界;一个对社会在相互连结上,更能成就其所需的世界。
这一个他所预见的世界,不是仅靠祈福就寄望得以实现。且这帖能够改善现况的良药,对我们现在的急迫性,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,都要刻不容缓。
本文摘自天下杂誌出版《柔软的心最有力量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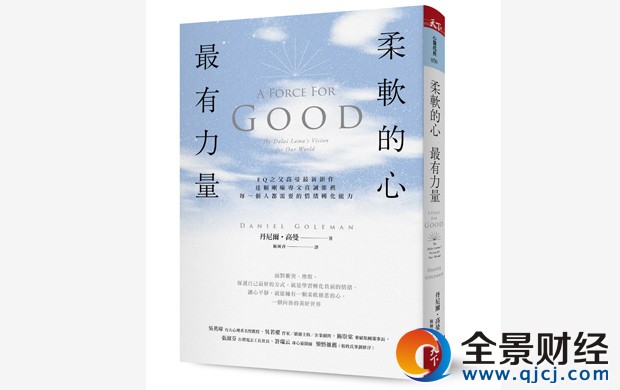
-
无相关信息











